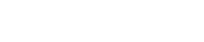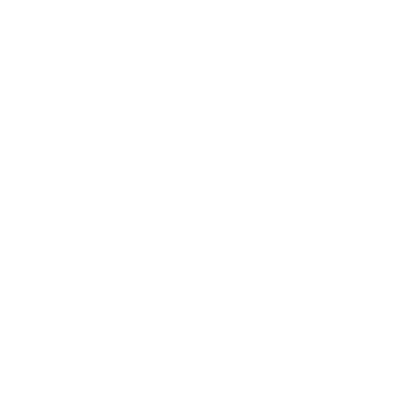訪問及整理:秦韻欣
以前會聽到人說「返鄉下耕田啦!」來取笑別人老土、沒有見識。現在,人們不用「返鄉下」也可以耕田,而當農夫也不一定老土。鄉土學社的農夫阿手──年輕、風趣的陽光男孩,與我們心目中的傳統農夫形象迥然不同。
阿手不是出身於農民家庭,四年前的他與不少香港職青一樣,朝九晚六在辦公室對着電腦幹活。不同的是,當大家認為這是有為青年的正路,他卻轉行做全職農夫。
一條乾的粟米成了他生命的種子
阿手當農夫前,在施達當了四年教育及推廣工作。在2009年,他有機會到訪泰北夥伴和當地的項目,開啟了他對農業的探索之旅。
「在泰北山區,看到很多家庭的門外掛上了一條乾的粟米,不明所意,細問下發現這是當地家庭用來警惕自己的。」原來,過去曾有商人到村裏,叫農民單一種植粟米,大量供應給商人。於是,整條村便改種粟米,放棄種植原有的作物。村民起初以為這是一條生路,但後來發現原來是死路一條。當粟米價格下跌時,商人沒有作任何補償,結果村民血本無歸。自此,他們便在門外掛上一條乾粟米,提醒自己不可再因一時貪念,只倚賴種植單一作物。
「一粒種子可以叫一條村衰落,也同時可以帶來發展。」成也種子,敗也種子,阿手驚訝種子的威力可以如此巨大,足以改變一條村的命運,燃起了他對農業的興趣。
回港後正值菜園村事件,激發阿手更多思考土地、耕種和生活的關係,認為縱使生活在香港,我們同樣需要一粒種子來建構生活和文化。後來,他參加了鄉土學社的農耕活動,多了關注食物問題,着重吃的是否安全、健康。「我們身體的感受是最重要,而由身邊的人種會更有信心,更是empower(賦權)自己去保護身邊的人。」當四年前鄉土學社需要人手,阿手便很自然地當上全職農夫。
歸園田居叫他體驗「得自由」
阿手現時在鄉土學社生活。說是生活,因為他不只在那裏工作,更以農田為家。他說到現時的生活型態與以往完全不同,現在會善用天然和周遭的資源,盡量減少消耗石油。例如,會用天然物資作清潔劑、使用柴火煮食、用蕉葉等天然資源包裝、活化垃圾站裏的可用物資、主要在農田附近的市區活動、從附近市墟收集菜渣和豆渣作肥料等。
與過去的辦公室工作不同,農耕完全受制於大自然,預先計劃好的未必能夠如期發生。除了天氣的無常,還要看土地的狀態。「與土地的關係很麻煩,糾纏不清。」阿手提到土地有時會是很好的狀態,有時卻會讓人不明所以。例如,田裏會突然出現很多蟲,但到某一時候又會突然絕跡。就如神其他的創造一樣,是那樣的奇妙和測不透,十分耐人尋味。在田裏工作和生活,不能夠單靠自己的能力,而是要與土地互相配合。
超貼地的農耕經驗,亦叫阿手對一段過去在施達服侍時經常引用的經文有新的演繹。「在路加福音4章18節『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』,為何不是說讓他們脫貧?自由和脫貧有甚麼分別?」務農讓他發現,自由不只是讓人擺脫貧窮,還有讓人可以自主生活。脫貧可能是協助受壓制的在主流世界和社會的制約中,走向一個較佳的位置生活,但仍然是在制約之下。而農耕則是跟隨四季、生態和土地的自然變化耕作,種多少便賣多少,阿手認為那就是自主,也是叫人得自由。
農夫的未來
說到未來,阿手說現時香港的農民較少交流,他希望可以認識更多本地農民,聆聽他們的故事;2018年會再到日本與當地農民交流種米技術,參考日本的做法。但說到最感興趣的,就是參與留種的工作。作物會按土地和種植的環境而改變,農夫可以按作物的產量、味道和外形,選取品種進行留種,經過一段時間的種植,便可以發展出一種最適合本地種植的獨特品種。「留種完全體現人與地的互動,我覺得好好玩。」
另外,阿手所屬的鄉土學社一直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人當全職農夫。「其實日本那邊很早前以有人提出『半農半X』的生活,一方面以自身的技術和才能(X)工作謀生和貢獻社會,另一方面自己種菜給自己食,食得安全。」阿手認為這種方式在香港也是切實可行的。
後記:夏蟲不可語冰
今次訪問,改變了我對農夫的看法,更發現人與土地的關係是可以如此密切。是的,我們太習慣於控制大自然,忘了神創造的萬物都是彼此配搭,相依共存;聖經中所提及的創造,亦是有規律和秩序的。當我們更多了解祂的創造,除了驚歎,也要學習謙卑順服,不能再作那條不知狀況的夏蟲。
今期《呼聲》目錄
整理和撰寫:潘文欣 甚麼是「發展」?怎樣的發展會帶來建立,怎樣的發展卻帶來破壞?或許泰國北部山區靠地維生的社羣,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。 綠色革命的毒害 居於泰北山區的拉祜族人,他們的先祖在過去為尋找適合的耕地,在泰國、緬甸與老撾三地遷徙移…
作者:黃國維博士(中國神學研究院助理教授 (神學科)、副教務長,施達董事) 「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。不是惡這個愛那個,就是重這個輕那個。你們不能又事奉神,又事奉瑪門。」 「所以我告訴你們: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,喝甚麼;為身體憂慮穿甚麼。…
傳統以來,兒童事工給我們的印象是向貧困兒童和孤寡給予助養、助學和生活援助。可有想過,兒童事工也可結合社區重建和農業發展? 過去60年,緬甸內戰不斷,加上連年天災,不少兒童因此失去家園,甚或至親。施達緬甸夥伴Full Moon於20年前設…
訪問及整理:秦韻欣 以前會聽到人說「返鄉下耕田啦!」來取笑別人老土、沒有見識。現在,人們不用「返鄉下」也可以耕田,而當農夫也不一定老土。鄉土學社的農夫阿手──年輕、風趣的陽光男孩,與我們心目中的傳統農夫形象迥然不同。 阿手不是出身於農民…